[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翻译/观察者网 彭宇萱]
随着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其内阁成员提名,各界纷纷讨论这些人事任命预示着下届政府对华政策将走向何方。
一些人推测,秉持“交易至上”理念的特朗普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并将此视为向务实的“以交易为导向”的中美关系迈进的窗口。另一些人则认为,特朗普厌恶战争,更倾向于将自己塑造为一位“和平总统”。就此而言,有预测认为,即便国会政客和华盛顿外交政策圈仍对中国抱有强烈敌意,但短期内美国与中国爆发冲突的说法也将逐渐平息。
推测性分析是政治评论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会剖析个人的言论,希望能洞悉当下的态度和未来的行动。与其仅仅聚焦于个人的言辞,试图把握某个人的可能或不可能的行为,不如通过重新审视美国外交政策圈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来洞察可能的态度和政策参数。我将此称之为“首都圈内环境”(Beltway Milieu)。
这一观点背后的预设是,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所处环境的产物,而且特朗普作为总统(及其行政团队)远非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局外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塑造。另一种思考方式是将其视为一个“行动范围”——即个体行动者能够或可能塑造其周围世界的空间,因此,他们能够考虑作为回应的各种可能性。
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史学家保罗·希尔(Paul Heer)近期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及他在一次私密会议中所收集到的反馈,这次会议讨论了美国及其盟友应如何在所谓的“印太地区”实施战略以“应对中国挑战”。希尔总结道,美国外交政策界对与中国和平共处毫无兴趣。
他观察到,“普遍的感受是,与中国的交往已变得极其棘手,甚至可以说是徒劳无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的战略野心几乎不给和解或和平共处留下任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受到指责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接着论证道,“许多与会者甚至认为,即便是中国的最低限度目标也是不可改变的,并且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无法调和”。
对于过去十年左右一直关注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多数观察者而言,这一基本立场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在2017年、2018年左右,政策制定者就已明确认为“接触政策”已经失败。
在2018年3月《外交政策》的一期特刊中,评估了过去数十年“接触政策”的有效性,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得出结论:“无论是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是地区平衡战略,都未能阻止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体系核心组成部分的企图。而自由国际秩序也未能如预期般有力地吸引或约束中国。相反,中国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在此过程中打破了美国的一系列预期。”在他们看来,中国“违背了美国的预期”。
2024年2月,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一次讲话中证实了这一观点,他哀叹美国数十年来试图“塑造或改变中国”的努力未能成功。接触政策只是实现更广泛战略野心的一系列战术手段之一,即“塑造或改变”中国。接触政策不应被理解为其他任何形式,也不应被视为实现国家间平等和平共处的途径。
 资料图: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AP
资料图: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AP
现实政治与美国对亚洲的态度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试图按照自身利益与期望来塑造中国。对于美国政坛而言,中国问题主要是关于改变、遏制还是征服的选择;而美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态度则取决于这一选择将如何影响其遏制中国的能力。台湾的地位在这一系列动态考量中尤为突出,至今仍在美国的算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纯粹的地缘政治和力量投射的角度来看,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在1949年和1950年败退的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岛之前,就已经将台湾纳入其规划之中。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开始考虑台湾的未来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到了1942年中,国民党政府明确表示希望战后能将台湾岛主权归还给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东亚事务司司长明确指出,台湾岛的回归是合理的,因为其人口大多是中国人,而且长期以来,该岛与中国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种私下里的情绪就在公开场合得到了宣扬,这或许是对美国媒体提出的将台湾岛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的建议的一种回应。
《开罗宣言》实际上确认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尽管如此,美国更倾向于由美国领导的军事政权,并推迟了全面主权的移交。换句话说,当时国民党在美国人眼里并不受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为台湾制定了征服计划和占领计划。尽管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实现,但这些规划充分表明了台湾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台湾被视为关键的军事资产,虽然美国曾计划攻击日本在台湾的基地,但也在考虑未来占领该岛的挑战。
到1944年中,美国为计划中的岛屿占领做好了人员培训的安排。在计划占领期间,美国海军被授权规划和管理该岛的民事事务。普林斯顿大学对这些人员的培训计划于1944年10月1日开始。
在上述规划与筹备工作进行之际,1944年春,华盛顿方面获悉,国民党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台湾的临时政府,并准备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省份进行管辖。虽然美国没有预料到国民党会在美国计划占领台湾之前建立任何形式的政府,但美国决策者对于确保美国的首要地位还是感到十分担忧。美国人认为,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迫使日本人投降,国民党在日本战败后没有能力妥善管理台湾。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一同在开罗举行会议。 新华社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一同在开罗举行会议。 新华社
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国民党是否应全权负责美国计划占领台湾的前线事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虽然认为听取中国人的意见和建议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美国竭力“防止中国进行不受欢迎的参与或干涉”,并宣称“必须严格坚持美国军事当局独家责任和权威”。(引自美国国务院记录,伦纳德·戈登(Leonard Gordon)1968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的论文《1942-1945年美国对台湾的规划》,上述叙述大量参考了戈登的论文。)
战后年间,随着美国致力于巩固其在“美国的湖泊”(即广阔的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并减轻苏联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及其在亚洲其他地区(如韩国)的立足点构成威胁的风险,台湾的军事战略意义愈发凸显。1950年6月,美国总统级别关于朝鲜局势的讨论便体现了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上,分发了一份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准备的机密备忘录,其中将台湾岛称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舰”。备忘录接着论证道,如果该岛屿落入苏联之手,“俄罗斯将获得一支额外的‘舰队’,其获取和维持的成本将远远低于十艘或二十艘航空母舰及其支援部队所需的成本。”在这种背景下,控制台湾岛是抵御苏联在亚太地区风险的关键屏障。
在麦克阿瑟备忘录发表后的15年,即1965年11月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给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美国对越南战争中的态度,这一态度是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下针对遏制中国而设定的。这一框架建立在对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安全直接威胁的担忧之上。麦克纳马拉论证道:
“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基于国内一种本能性的认识,即亚洲的人民和资源可能会被中国或由中国牵头的联盟有效动员起来对付我们,而这样一个联盟可能带来的潜在分量,会使我们陷入被动防守的境地,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他辩称,中国“正逐渐崛起为一个主要大国,削弱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而且更长远也更可怕的是,它可能会联合整个亚洲与我们为敌。”现在看来,这份备忘录仿佛就是今天所写!
该备忘录旨在概述一系列可加以利用的军事战略方向以遏制中国,同时避免激起中国或苏联的“强烈反应”。这份备忘录是美国政治界当时对亚洲局势所持态度的象征,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影响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关切的评估标准。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美国深陷印支冲突,因此几乎没有能力响应蒋介石要求美国援助以实施其针对中国大陆的各种收复计划。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些提议遭到了拒绝;美国在其他地方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不支持开辟新的战场。尽管美国态度冷淡,但在1966年,蒋介石仍坚信反攻大陆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再次向美国寻求支持,但再次遭到拒绝。美国在其他亚洲地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而且美国政治精英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考虑采取重大的现实政治行动,即从“中华民国”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更广泛地迂回包围和孤立苏联努力的一部分。
尽管美国仍有不少支持“中华民国”或“反共”的顽固分子,但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受到了冷战和其他地区压力的制约,这些顽固分子只能等待时机。
到了1969年,自1949年以来蒋介石所采取的明确进攻态势,已转变为“攻防结合”的战略立场。这一更为模糊的立场,最终在1991年台当局发布所谓“国家统一纲领”后,被明确的防御姿态所取代。此时,正如Takayuki Igarashi在2021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所论述的,台当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以武力收复大陆的战略。当然,这时的“中华民国”已失去了美国和联合国的正式承认。
20世纪60年代末,现实政治影响了美国的态度,最终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广为人知,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与中国开展对话的主要驱动力是获取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1970年12月,基辛格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阐述了这一战略思维的本质。他指出,苏联希望与美国对话,以减少“西线”的牵绊,从而应对东部的中苏边境冲突。仅仅通过让苏联知道美国正在“重新审视中国问题”,美国就能够在与苏联的关系中获得相当的杠杆作用。与中国的对话,首先被美国设想为用作制衡苏联的力量。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机场握手。 新华社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机场握手。 新华社
精神之战与中国“失陷”
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对美国来说不仅是一次地缘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深刻挫败。“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在国内政治上揭开了旧伤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杜鲁门政府因其在对华政策上的无能而备受指责。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25年的时间里,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人,将其视为有待拯救的两大目标之一。传教士涌入中国与新殖民主义的传教计划紧密相连,该计划源自以救世主国家自居的、具有公民宗教传统的美国。如勒内·霍尔瓦斯特(Rene Holvast)在2009年所述,这项任务旨在克服所谓的“10/40地平线”——即10度至40度纬线之间的地带,基督教尚未立足且力量最弱的地方,覆盖了北非、中东、印度、中国和日本。
1940年代,在这种传教热情的推动下,传教士在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了1950年代初,一些传教士认为继续留在中国已不再可行,那些没有返回祖国的传教士,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撤退,前往台湾或香港。
美国对台湾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承诺体现在蒋介石及其夫人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洗礼的事实中,他们被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视为“为我们而战”的人。在1950年的一次演讲中,麦卡锡在抨击约翰·S·谢伟思(John S.Service)向共产党投降的行为时——这是他关于美国国务院内共产党人演讲的一部分——他指出:
“当蒋介石在为我们而战时,国务院在中国有一名年轻人,名叫约翰·S·谢尔曼。他的任务,显然不是致力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化。然而,奇怪的是,他却向国务院发送官方报告,敦促我们暗算盟友蒋介石,并声明,共产主义是中国最好的希望。”
麦卡锡已踏上了他的征程,誓要揭露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影响。他的反共运动与中国战争局势的动态交汇,最终与美国对中国“失陷”的深切哀叹不谋而合。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一事在美国选举政治中被恶意政治化,这不仅从地缘政治(反共主义)的角度,更从精神层面界定了美国的利益。麦卡锡在那次演讲中辩称:
“如今,我们正处于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之间的终极决战。现代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已选择此刻作为决战之时。各位,此刻已到了紧要关头——真正的紧要关头。”
因背叛而局势危急。“中国失陷”既是国内问题——我们中间有叛徒,也是世俗打击——一边是基督教,另一边是共产主义无神论。这些千禧年论与末世论的潜台词,与摩尼教式的狂热信仰相混合,在更广泛的冷战环境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精神战争。这场精神战争通过“40/10”框架获得了空间形态,该框架界定了福音基督教被认为代表不足且势弱的地区。
 资料图:约瑟夫·麦卡锡
资料图:约瑟夫·麦卡锡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地区,反而成为了臆想中的“强大恶魔势力的领地或据点”。为了进行传教,理想情况下是在2000年之前必须推翻这些势力(见O’Donnell的观点)。精神战争的地域化加强了当时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偏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至今仍在美国对华(包括对台湾地区)态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热情的福音派信徒而言,领土上的皈依预示着上帝在地上王国的建立,并为基督再次来临的高潮奠定了基础。
台湾在这场领土与精神的布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58年初,曾任台湾驻日代表的沈觐鼎在美国向一个基督教团体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的基督徒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他当时正试图动员美国基督徒支持台当局正在进行的收复大陆的努力。
这场政治斗争绝非寻常,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精神之战。他认为,就美国利益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利益相一致而言,必须支持台湾岛上的力量,以促成大陆的光复。因此,他论证道:“在台湾省,基督教会强大而自信地生存着。在与大陆分离的这些年里,台湾的基督教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台湾显然被视为往昔美好时光的遗存,同时也预示着未来更加美好的时光。“台湾省”成为了基督教得以发展和繁荣的避风港,为了说明基督教在该岛上繁荣发展的程度,他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他告诉听众:
“1945年,台湾在历经日本半个世纪的统治后归还中国时,岛上的基督徒人数不足三万。当时只允许少数几个教派活动,其中最活跃的是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团。如今,台湾已有超过100个基督教教派在活动。在短短12年间,基督徒的人数从三万增加到近三十万,增长了近十倍。”
他证明了在仅仅12年的时间里,岛上基督教信徒的数量增长了十倍。请注意,他承认台湾是在二战结束时由日本归还给中国的。
对他来说,台湾是基督教的灯塔。他描述了他在台北所参加的士林教堂的一个“普通的星期日”的情况,明确地将政府的合理性与其精神导向联系起来,并特别指出蒋介石夫妇是教堂中引人注目的常客。台湾是一个精神上的堡垒,也是基督教使命再次启动的平台,旨在重新确立基督教在大陆的传播地位。反共斗争也是基督教的集结口号。台湾不仅仅是一个不能落入苏联手中的不沉航母;它更是中国精神战场上的一处突破口,因为从这里可以再次发起对中国大陆的精神战争。
接触政策:目标相同,手段各异
接触政策是美国近期追求其抱负的具体表现,其目的在于,希望凭借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秩序——即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辅以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最终推动中国发生政治和文化变革。
在最近几十年接触政策实施之前,美国对中国的立场受到了周期性偶发事件的影响,比如基辛格和尼克松想要超越苏联的意图,以及在此之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共产主义在整个亚洲传播的担忧。在那几十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被深深的悲痛感所框定——“谁失去了中国”是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尖锐问题。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同时,冷战背景下一部分的精神战争心态也开始出现。这一背景下,“失去中国”这一事件一直刺激着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的野心在于弥补这一“损失”,利用台湾岛作为抵御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堡垒,并可能将其作为针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跳板。这座岛屿既是地缘政治上的“不沉航母”,也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撤退到岛上的传教士精神大军的根据地。
如果不能依靠武力夺回中国,那么就要通过传教工作来努力争取。不论是基督教,还是退而求其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义,其目的都是要将中国人的灵魂从马列主义那“非自由”、“无神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然而,面对坎贝尔和拉特纳所描述的中国人的反抗,这些旨在“塑造或改变”中国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美国政治圈的反应是放弃接触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对中国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敌意被激发出来,国会为反华宣传拨款16亿美元(2024年9月)更是加剧了这一敌意,这股敌意是长期受挫的野心与千禧年例外主义的冲动相结合的产物。
通过经济制裁和各种禁令来实现脱钩;在美国教育和研究机构中追查中国“间谍”;以及正如李成(Li Cheng)在2024年10月25日《金融时报》中的观点,对试图了解中国日益表现出矛盾心理——这些都表明了一种政治文化,美国坚信自己的优越性,并对中国拒绝屈服感到愤怒。
制裁和关税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他倾向于将关税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他的亲信、《没有自由贸易那回事》一书的作者罗伯特·莱特希泽正在积极游说议员,认为加征关税是阻挠中国、振兴美国产业的必要之举。莱特希泽主张齐心协力,实现与中国的经济脱钩,一举削弱中国、强化美国。对莱特希泽而言,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必须采取积极手段予以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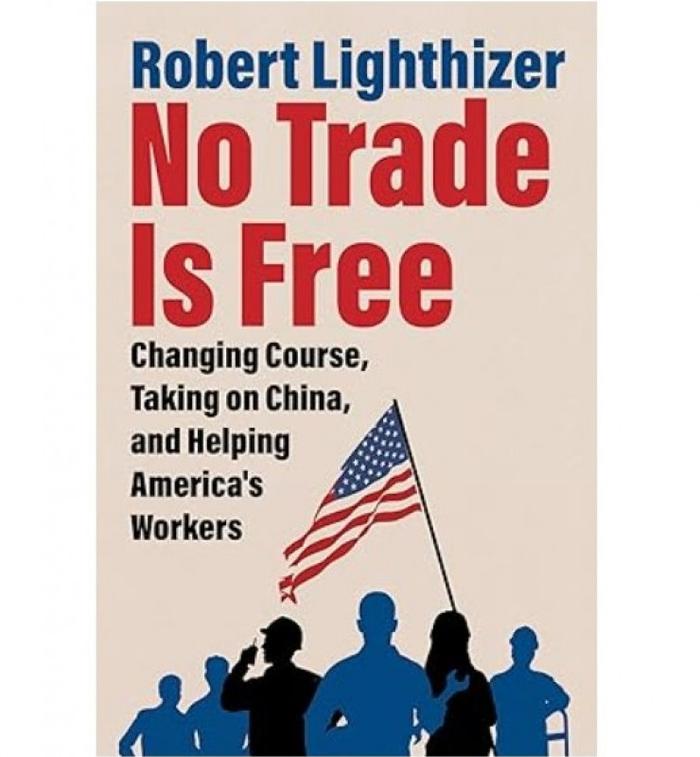 No Trade Is Free 《沒有自由贸易那回事》
No Trade Is Free 《沒有自由贸易那回事》
另一些人则更加激进。2024年5月至6月间,博明(Matt Pottinger)和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拜登政府过于关注围绕“管控竞争”概念展开的短期战术问题,而实际上,关键在于要实现对中国的全面胜利。对于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博明,以及身为众议员兼众议院中国共产党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的麦克·加拉格尔而言,这意味着要推行政权更迭战略。美国曾失去中国,现在必须重新塑造中国。
特朗普的论调和首都圈内的氛围并不相悖。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本人的观点助长了这种氛围,而这种氛围又反过来影响着政治格局,进而塑造了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互动的动态。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而非针锋相对的。
首都圈内部弥漫着憎恶与好战的情绪。中国被指责为美国国内困境的罪魁祸首,并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挑战。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将中国塑造成自己的模样,想要夺回被共产党“夺走”的中国。中国拒绝屈服,这本应是希尔所描述的“相互妥协”必要性的生动一课。但华盛顿从不愿妥协,其千禧年的狂热和重燃的精神战争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特朗普能否跳出这个政治环境并重塑其氛围,还是政治环境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找到体现?这是当今时代的问题。
责任编辑:刘德宾


